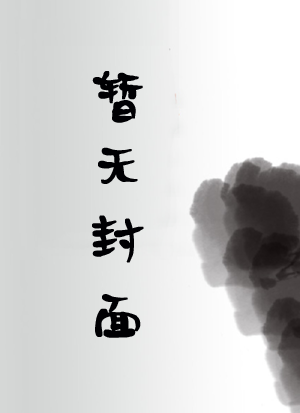随着時間推移,入京的修士越來越多,栖凰鎮上人頭攢動,場景不下于年關時分的廟會。
栖凰谷内也是人滿為患,大丹朝稍微有點名望的修士,基本都出自栖凰谷;回師門叩見師長,不可能住外面,客房滿後,些許輩分小的弟子還得騰出房間,和師兄弟擠一個屋。
雖然沒了往日的清淨,不過這‘萬宗來朝’的盛況,還是讓谷内弟子覺得與有榮焉,再怎麼說,雞頭也比鳳尾強嘛。唯一美中不足,就是天公不作美,又下起了綿綿春雨,栖凰谷不似仙家豪門有護宗大陣,一幫子‘仙長’‘道友’在谷内淋着雨客套,稍顯不體面。
吳清婉是丹器房的掌房,三十年前學藝之時,也是從弟子輩混過來的,這次過來湊熱鬧的人中,還有不少是她同屆的師姐妹。舊友重逢免不了回憶往昔,這幾天都沒能閑下來。
中午時分,吳清婉好不容易送走了過來探望的師妹,便接到大師兄的傳喚,撐着油紙傘離開竹林。
雖然下着雨,山谷内的廊台亭榭間,依舊能看到不少人打坐修行,有些人甚至冒雨露天坐着。
栖凰谷内的靈氣,自是比不上那些大宗門,但也是一塊能支撐幾千人修行的風水寶地,比谷外濃郁得多;這些人往日進不來,此時也是趁着機會蹭靈氣。
修行皆不易,東道主也得有東道主的氣量,吳清婉自然也沒表現出不滿的地方,偶爾遇上認識的師兄,還會颔首打個招呼。
殿前廣場上已經搭建好了很多席位,雨幕之下人頭攢動,不少年輕修士在廣場上切磋,也有長者在旁指點。
修行一道,不全以戰力論高低,一輩子不殺生隻救人的‘醫仙’也不是沒有;但大丹朝修士九成都出自栖凰谷,說起來都是武修,這次挑選優秀弟子去驚露台,唯一能服衆的方式,也隻有比拼戰力了。
吳清婉緩步穿過廣場側面,沿途也在打量着這次過來的年輕人,看有沒有能和左淩泉媲美的。
隻可惜看了一圈兒,無論相貌、身材還是氣度舉止,沒有一人能摸到左淩泉膝蓋。
對此,吳清婉心裡還有點小得意,不過她還沒得意多久,就聽見了一些不和諧的聲音:
“……我那堂弟是真傻,跟老陸你學多好,非跑來這地方拜師。你看看這些個繡花枕頭,劍耍得還沒我好看……”
“唉……”
“老陸你歎啥氣?我這是在說你教得好,你聽不明白?”
“?”
……
大丹朝用劍的修士,基本全出自栖凰谷。吳清婉聽見這話,自是有點不滿,轉眼看去,才發現廣場邊上站着一老一少。
老的腰懸佩劍,戴着鬥笠背着手;少的勾着老的脖子,擡手在指指點點。
吳清婉随意打量了下,看不出什麼特别的,也不認識,便也沒搭理,直接進入了正殿。
正殿之中已經有不少人,都是大丹朝各地的長者。栖凰谷的四位師伯,在最前方就坐;正對大門的巨幅畫像下,站着的卻是個身着黃袍的中年男子,手持三炷清香,正恭恭敬敬地給畫像敬香。
吳清婉瞧見此人,眸子便微微眯了下,認出了這是扶乩山的掌門程九江。
扶乩山建宗的年月,隻比栖凰谷晚一些,在大丹也算曆史悠久的修行宗門。不過其祖師爺是關外的散修出身,功法傳承得自九宗之外的宗門,所以一直不被朝廷和修士看重;扶乩山也隻是一座靈氣充裕些的小山,難以供給太多弟子,人數也常年維持在六百人左右。
雖然人少資源少,但當代掌門程九江也算個厲害人物,甲子之齡比栖凰谷大師伯還年輕,修為卻入了靈谷四重,是整個大丹排第二的強者。